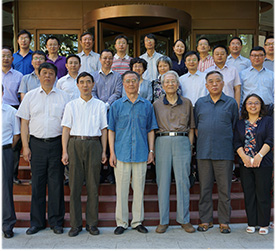[内容摘要]: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汉墓;汉画;列仙图谱;《真诰》;汉代宗教
神仙思想长期盛行于战国秦汉,可以想见当时应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应的仙谱(不一定以谨严的文本形式传世),以教人信仙之实有。然而在现有的一般概念中,“仙谱”似乎就是《列仙传》、《神仙传》、《位业图》乃至《仙鉴》之类的道教文献。在《列仙传》之前,是否还有更早的仙谱?其构成、标准、秩序如何?这个问题至今未被触及;且其形态究竟如何,遍寻古籍难窥一斑[1]。事实上,大量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和壁画,已提供丰富数据,只是其真实属性长期不为学界所识,因而阻碍了对隐藏其中的汉代仙鬼谱系的把握。
汉画中经常出现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山灵海神、奇禽异兽、风伯雨师、仙童羽人等神仙灵异的题材。这些图像向我们证明,那里是鬼神的世界。与此同时,汉墓中往往以特定故事情节的图像叙事方式刻画某些帝王将相、孝子贞妇、忠臣义士等历史人物;古时博物家对此已有关注。《水经注·济水》引戴延之《西征记》记述东汉鲁峻(公元111-172年)墓云:
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2]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历史人物为何被选入墓葬画像之中?对此,学界一直局限于“历史故事”的世俗认知框架,尽管也认识到这些人物之被选择乃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驱动的结果[3]。
这种认识方式的致命问题,是忽略了墓葬的宗教属性。人死为鬼,故《说文解字·鬼部》说“人所归为鬼”;在神仙思想支配下形成的汉墓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神鬼世界;墓中刻绘的历史人物,不复以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已成神仙;墓主人自然与他们一起生活在鬼神所属的另一个时空。在纷繁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形态背后,是否隐有某种内在的宗教的规定性?
一、“视万龄如旦暮”:神仙世界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
山东省沂南县北寨东汉画像石墓中室南壁西段的一幅画像石,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刻齐桓公、卫姬等人物,当取“卫姬请罪”之故事情节。至于下格所绘,《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则出现如下的困惑:
下格刻着三人。左面立着一个戴有布纹的帽子的人,身佩长剑,双手扶住一有缨套的长矛,上有榜刻“齐侍郎”三字。……中间一人头上有榜,刻“苏武”二字;右边一人头上榜刻“管叔”二字。管叔是周初人,苏武是西汉时人,侍郎是汉代官名,这表示这些榜题是乱刻的。[4]
另外,沂南汉墓画像中还刻有孟贲(秦武王时的力士)与蔺相如(秦昭王时)同堂共事,《报告》亦以为“乱刻”。这些不同时代的人物,在画面中比肩而立,令人困惑。事实上,细观汉画,类似现象多见,必须正视、深思。墓葬乃至为肃穆之所在,面对大量奇特图画,“乱刻”二字何堪了之?又有观点认为,诸如此类的安排,“一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或一知半解……;二是有意所为。如将苏武和管叔组合在一个画面的目的在于,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将蔺相如的无畏、孟贲和三力士的力大无穷组合在一起,显示力量的强大。以此装点墓室,在教育借鉴之外,增加辟邪的威力。”[5]现在看来,此中尚有更深的原因,这个原因——如果存在的话——的隐蔽性本身表明它更具内在规定性。
欲判此中人物是否为“乱刻”,先须辨明汉人在墓室内刻画历史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一现象,同墓葬本身的关联逻辑。若仅为装饰墓室,或为纪念那些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按照汉人的丧葬逻辑,显然这些不应出现在墓葬之中——诸多汉墓出土资料显示,东汉时人们关于生前、死后的空间所属已形成严格区分且多忌讳[6],墓葬非为生人而作,其内容当然也无法正常观看[7],所以不存在单纯“装饰”或“纪念”的可能。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云楶藻棁,龙桷雕镂。飞禽走兽,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奋衅而轩鬐。虬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躨跜。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蟉虬而绕榱。白鹿孑蜺于欂栌,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跧伏于柎侧,猿狖攀椽而相追。……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仿佛。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媱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8]
有学者认为“从灵光殿这一名称和其内部的壁画内容推测,这座宫殿绝不会是刘余及其家属日常居住和生活的宫殿,极有可能是当时鲁国的宗庙”[9]。确有可能。其他祠堂如武氏祠、宋山小祠堂等亦是地面建筑,其画像之主要观众还是生人,尽管墓祠之功能最终非为生人,其主题内容也是“神仙灵怪”、“古之圣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如此则汉代社会中同样以这些为常用的绘画题材,甚至还有淫妃乱主等反面教材,以图“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之效。
然而,如《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提到的沂南汉画中“苏武”、“管叔”与“齐侍郎”同堂比肩的情景,显然并非用以载叙历史,若是出现于世俗绘画作品中,自属“乱画”;但若沿此逻辑以墓中所见为乱刻,则不免拟俗臆断之嫌。
坟墓乃去世者之所居;研究汉代墓葬画像,须特别注意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下的时空观念及其对于人物的不同规定性。墓、祠中的汉画及俗间的绘画题材,世俗所见或为历史人物故事,而当时主持此等事务的道者术士,则必有所本。这正是需要学者努力揭示的方面。宗教的奥秘就蕴藏在对世俗经验逻辑的超越之中,——哪怕是以荒诞的方式。因为墓葬的最终目的,是要回答死者而非生者的终极诉求。经过宗教的“过渡”,无论其人生前的时代(时间)、地域(空间)有何等的差距,死后都可超越俗世时间逻辑与空间秩序的局限,而进入同一时空的神灵世界。汉人在墓葬中刻画历史上那些早已故去的人物共处同一时空,是要表示,死者将进入神仙世界,加入那个不朽的行列。基于宗教研究视角的整体考察而得出的这个结论,在以下的具体讨论中将一再得到证实。
颇为难得的是,萧绮在为《拾遗记》卷二所写的“录”中,合理地解释了来自不同历史时空的人物何以能得比肩共处:
观伏羲至于夏禹,岁历悠旷,载祀绵邈,故能与日月共辉,阴阳齐契。万代百王,情异迹至,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10]
可见,汉画中出现的俗间难以想象的奇景异象,包括日月同辉,“人”仙共处,水天一片(鱼车、龙车、雷公、风伯出现于同一画面空间),怪诞身形(兽首人身、人首兽身、多首)[11]等,无不表明,画面所表现的,正是超越俗世经验的鬼神世界。
同样的道理,汉画中将“管叔”、“苏武”等不同时代的人物刻在一起,虽不符合世俗的历史逻辑,却合乎特定的宗教神学逻辑,所以才会如此描绘他们比肩共事于另度世界。更进一步说,基于墓、祠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属性(死者所居),汉画中的“古之圣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历史人物,实际上已被赋予象征死者在死后世界获登仙品的宗教功能。换言之,汉画中的历史人物画面,绝不是表面似是的劝善“教材”,而是当时社会价值标准被推向极致的宗教化样态——一套基于儒家忠、孝、节、义伦理的秩序严谨的神仙谱系,用之于墓中,意在表示死者也将跻身其列。遗憾的是,有关汉代这一仙鬼谱系的文献记录未能保存下来,使后人在汉代画像的理解中面临重重障碍。
二、汉画中的仙鬼谱系:以武梁祠东、西、后壁图像为中心
关于武梁祠东壁、西壁、后壁画像,吴曾德指出,画像“包罗了三皇五帝等十帝王像、周文王十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刺客豪侠、孝子贤孙、贞节烈女等故事像,堪称历史故事画廊”[12]。巫鸿提出:“一个似乎让人费解的现象是,在这部分图像中,性别、德行以及社会身份不同的各色历史人物相杂一处,明显有别于上部装饰区域中对人物的清晰分类。这里,围绕中心楼阁刻画着六个刺客、两位贤相和一位列女。更令人迷惑的是虽然如上层图像中的女性人物,钟离春的故事也出自《列女传》,但她却被单独放在这里,与其他女性形象分开。这种安排是不是有意设计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什么因素把这位列女和忠臣、刺客安置在同一组图像中?又是什么因素把这些历史人物和中心楼阁及其相关的题材连在一块,编制入一个更大的构图中去?”[13]
如上所述,汉画中为数不少的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恰恰是强烈表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非世俗特征。以此观之,在战国以来神仙思想的长期熏染下,汉画中与众多常见的神仙奇异图像处于同一图像语境的“历史人物”,应即超越世俗经验的仙鬼;从画面可明显看出,他们之间存在高下之别,表明这个仙鬼世界存在一定的等级秩序。进一步说,汉画中包括帝王将相、王公王妃、圣贤高德、忠臣孝子、英雄列女在内的人物,乃是一个秩级有序的仙鬼谱系。
实质上,武梁祠西壁、东壁及后壁画像(图像内容的文字整理见表1)[14]可以说是汉代列仙图谱的典型呈现,为把握汉代仙谱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依据。三面石壁均被菱形纹、连弧纹分隔线分为三个大层,三石画面同层为同级:最上层三角形区域为西王母、东王公及神怪异兽,其与下层的分隔线除了菱形纹、连弧纹(嘉祥宋山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所谓“搴帷反月”,表示仙宫的帷幕)之外,还多了一层云纹,表明此上乃是九天神界,是最高神之所在(见于东、西壁的同一层),也是宗教性内涵最明显、最具本质规定性的图像区域;其下一层为帝王圣贤、孝子孝孙、节妇列女(见于东、西壁的同一层),处于同一重天宫帷幕之下,为第二等的神仙;再下一层为次一等的神仙,所绘为刺客与周代诸侯(亦见于东、西壁的同一层),为第三等的神仙(明主+英雄+贤相)。九天神界中,西王母、东王公、玉兔、有翼仙人等图像内容,宗教性内涵明确而突出,并因此成为具有语境规约性的图像层,在其下逐次展开的图像也因此具备神仙时空的属性——图像中区分人物上下的云气纹也暗示了这一点(这与暗示西王母所主仙界的马王堆外棺表面云气纹具有同样的含义,尽管形态有所不同)。以下依据汉代思想文化背景,探讨帝王、圣贤、孝子、列女、刺客等图像的具体内涵及排列标准[15]。
表1 武梁祠三面石壁画像内容整理表
| 西壁 | 第一层 | 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桀(从右至左,下同) |
| 第二层 | (曾母)曾子,闵子骞,老莱子(莱子母、莱子父),丁兰 | |
| 第三层 | 管仲、齐桓公、曹子劫桓、鲁庄公;二侍郎、专诸、吴王(僚);荆轲、樊於其(於期)头、秦武阳、秦王 | |
| 后壁 | 第一层 | 梁高行(奉金者、使者);秋胡妻、鲁秋胡;鲁义姑姊(兄子、义姑姊,姑姊儿,齐将军);楚昭贞姜(使者) |
| 第二层 | 伯瑜(瑜母);(渠父)邢渠;(永父)董永;蒋章训?(章孝母);朱明[朱明弟,朱明(儿),朱明妻];李善;金日?(休屠像,骑都尉) | |
| 第三层 | 蔺相如(秦王);范雎(魏须贾) | |
| 东壁 | 第一层 | 梁节姑姊[长妇儿,梁节姑姊,捄(救)者,姑姊儿];齐义继母[追吏(骑),后母子,前母子,齐继母,死人];京师节女[京师(节)女,怨家攻者] |
| 第二层 | 三州孝人;羊公(乞浆者);(汤父)魏汤;颜乌;赵徇;(孝孙父)原榖(孝孙祖父) | |
| 第三层 | 要离、王庆忌;豫让、赵襄子;韩王、聂政;钟离春(齐王、无盐丑女钟离春) |
(1)“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帝王及刺客图
武梁祠帝王图所列十一位古帝王,从右至左分别为伏羲与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俈)、帝尧、帝舜、夏禹、夏桀。这十一位帝王,除夏桀外,或具文明开创之功,或是品行高超的“圣王”,故得高居仙谱上端。然而夏桀与另十位上古圣王比肩在列,备极庄严,令人甚感意外。
一般认为,夏桀作为有名的暴君与其他诸圣王并列,刻于祠堂,乃取其教化、劝诫意义;即夏桀是作为“反面教材”的典型被选择。这种论点看似有理,却很难经受推敲。帝王图中,除夏桀外,都是图像旁刻“人名榜题+赞记”的模式[16],而夏桀只有榜题,独缺赞记。如果刻画夏桀的动机在于树立反面教材,那么“赞记”自不用刻,但劝诫之类的表达岂不正应理所当然地书写吗?在本来可以宣示教化的地方却戛然而止,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缄默”。再者,如果确实意在教化,那么桀、纣连举应更合惯例,为何会在“反面教材”本已不足的情况下还只举其一?(有德的圣王十位,“暴君”只此一位)因此,“劝诫”说存在难以说通的逻辑缺陷,夏桀被列入帝王图应别有他因[17]。
夏桀在东汉得入帝王图,当与其拥有众圣王所不具的特殊勇力有关。而从传统史籍文献中确可发现有关夏桀惊人勇力的记载。《墨子·明鬼下》:“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勇力之人,生裂兕虎,指画杀人。”《淮南子·主术训》:“桀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谓:“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18]
从当时的整体思想、文化氛围来看,汉人也的确特别强调趋近“原始”的勇力与“霸道”,以能力、德行并重,故云“以霸、王道杂之”[19]。而这种标准当源自汉儒所崇的《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故东汉崔寔曰:“量力度德,《春秋》之义。”(《后汉书·崔寔传》)这个“能力”在评价个人的时候自然也应包括个人的力量;毕竟,在冷兵器时代,男子的强壮体魄对于国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秦汉尚力;尚力即尚武,帝国所倚。秦武王可谓其极,《史记·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竟因比赛举鼎过重致双眼出血、折断胫骨而死。徐州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力士画像[20],一人执盾挥剑,一人骑虎,一人怒目圆睁将树连根拔起,一人捉住牛尾倒背大牛,一人举鼎过头,身后跟随有抱羊者、抱壶者,生动表达了汉人对于力量的崇尚。正是因为骁勇的樊哙在鸿门宴上闯帐救刘邦,汉家才得以立业。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汉代尚武、尚侠之风的盛行[21],此种风尚浸入宗教思维,成为与忠、孝、节、义思想并行不悖的重要内容。
据此推测,夏桀可能是作为古来帝王中的“勇力”代表而被选入帝王图。夏桀像无赞记,表明尽管汉人尚勇,但在长时期积淀的崇德氛围下,仍然无法对其明言褒赞,所以虽然将其列入帝王图,给他与其他帝王的同等地位,作者却缄默而未附赞。这也表明,尽管存在董仲舒“《春秋》以为戒”的说法(《春秋繁露·王道》)[22],但从图像的整体逻辑及当时社会的思想背景出发,以尚勇、好侠且不回避“霸道”的角度去理解夏桀跻身于帝王图的原因,似更合理。
与此同时,在整体的图像语境中,夏桀以“勇力”得入帝王图,亦与下文即将讨论的众刺客(并见东壁、西壁图第三层)进入汉画之中的信仰逻辑相同,还与汉画中刻列诸“有英雄之才者”(《真诰·阐幽微第二》)的标准相一致(详见本文第三部分讨论)。譬如上揭沂南北寨汉墓画像中,孟贲与蔺相如二人被刻在一个空间里,比肩而立。事实上蔺相如作为赵国的使者去面见秦昭王的时候,孟贲早已去世,不可能一起出现于秦庭。将此二人画在一起,既不是“画家的联想”,也不是某种艺术手法,而是因为汉人相信在死后世界他们可以相遇;他们被归在同一个空间里,是因为他们符合相同的成仙标准。历史上,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齐人孟贲勇武过人、生拔牛角,其人格特征甚合汉代文化气质取向,堪谓“以霸、王道杂之”的汉人所崇“力”与“德”的典范,为“有英雄之才者”,故得图画而入“仙谱”。
又如河南出土的一方汉画像砖[23]显示,燕国上将军乐毅、燕昭王与宰相郭隗也在死后成仙,一同共事;此三人死后能再度相聚,是因为他们生前的为人,可谓君尽其英明、臣尽其贤勇,至为汉人所崇[24]。这块画像砖画面完整,布局规整、均匀,自成一体。不过仔细观察画像砖的图像安排,居中的不再是燕昭王,而是王相郭隗,乐毅和昭王则在其左右,可见汉代仙谱乃基于生前事迹的再评价而作。《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保存了这种再评价的例证:“汉高祖为南明公宾友。……荀彧为北明公宾友。……不拘职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为称量处分耳。”[25]如本为家奴的李善被刻画在汉墓的孝子类画像中,在《真诰》卷十六亦得叙列仙位(详见下文)。从文献记载和汉墓所见可以判断,在汉代思想中,世间的君臣尊卑秩序在死后失效,人死后在仙鬼中的地位,不依在世职位之高卑,而据生前所积罪、福之多寡来重新论定。
有意思的是,陶弘景注《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曰:“《剑经》序称,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国时英主,遂不堕于三官。”[26]而陶撰《真灵位业图》将燕昭王安排在第四层左位之中。现在看来,《剑经》及《位业图》应保存、继承了汉代关于燕昭王成仙的资料[27]。
如上所述,汉画中大量“刺客图”的出现,同样出于“有英雄之才者”得仙的汉代价值观。如表现“二桃杀三士”故事的画面常见于汉画,其文本记载见于《晏子春秋》卷二[28]。从该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晚期士人“重义轻身”的价值观念,他们极其看重仁、义、勇等道德价值,不惜以死相求。《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论衡·定贤篇》亦云:
人之举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势贯山。……天下之士不以荆轲功不成不称其义,秦王不以无且无见效不赏其志。志善不效成功,义至不谋就事。义有余,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细小,智者赏之,愚者罚之。必谋功不察志,论阳效不存阴计,是则豫让拔剑斩襄子之衣,不足识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载也;张良椎始皇,误中副车,不足记也。三者道地不便,计画不得,有其势而无其功,怀其计而不得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贤,三也。
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等抱定“一去兮不复返”之心,为国忘我、不计生死,强烈地表现出舍身尽命以求大义的崇高气节。而在宗教中这恰恰被认定为成神成仙、走向不朽的极端方式。陶弘景曾质疑:“自三代已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鬼中不见殷汤、周公、孔子、阖闾、勾践,春秋时诸卿相大夫,及伍子胥、孙武、白起、王翦,下至韩信项羽辈,或入仙品,而仙家不显之。”[29]这里“自三代已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之说,接受了汉以来的上古圣贤及英雄成仙的思想。汉代史籍文献与画像数据交互印证显示,荡平九州、诛暴整乱的霸主、刺客等英雄人物、忠勇贤能,在汉代皆为士人景仰的楷范,死后已入不朽的仙界。“或入仙品,而仙家不显之”一句,说明陶弘景认为以上提到的英雄人物自然符合升仙的标准(亦是延续汉以来的标准),也许已入仙品,而未见于仙家文献。事实上,殷汤、孔子、吴王、孙武,在陶弘景之前数百年已见诸汉画,在汉代神仙体系中各占一席之地,惟其深藏汉墓之中,陶氏不知耳;如汤王见于山东莒县东莞镇东莞村汉代圆孔碑阙正面[30],孙武见于河南密县出土的榜题“孙自(子)”的汉画像砖和山东兖州市博物馆藏榜题“孙武”的画像石[31],吴王见于山东嘉祥纸坊镇汉墓画像石[32]。周公往往以汉画常见的“周公辅成王”模式出现。这里所举著帻冠侍立带榜题周公画像,是大东文化大学书道研究所藏“宇野雪村文库”的一幅拓本。汉高祖刘邦和贤辅张良,则见于雅安高颐阙正面的高祖斩蛇和张良椎秦皇的雕刻画面[33]。
(2)“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臣、孝子与列女图
除帝王、英雄、刺客图外,忠臣、孝子与列女图亦是广泛见诸汉画像石的重要题材。如下文所论,这类图像同样需要置于汉代普遍价值观及其信仰背景中去理解。在武梁祠东、中、西壁成体系的图像排列中,这些“历史人物”有规律地分布在第一、二层,表明他们与圣王、英雄一样,在汉人价值体系中,已列仙位。如后壁第二层所刻李善乳主的著名故事[34],即表示李善已因生前的忠孝之德而成仙。实际上,这种思想早在《孝经》中已显露端倪——《孝经》用天人感应论建立起孝能通神的信仰,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但以汉画作为载体(亦或方式)的表达,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宗教化。《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曰:
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鸟山兽巡其坟埏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贯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变炼者甚多,举此二人为标耳。
就此陶弘景注曰:“比干剖心,可为至忠。至于孝子感灵者,亦复不少,而今止举李善,如似不类。当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迹也,恐以其能存李元后胤,使获继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不论耳。若程婴齐孙杵臼,亦应在孝品矣。李善字次逊,本南阳育阳李元家奴。汉建武中,元家人之死尽而巨富,唯尽一孤儿名续祖,尚在孩抱,诸奴复共欲煞之而分其才(财)。善乃密负续祖,逃瑕丘山中,哺养乳,乃为生计。至十岁余,出告县令钟离意。意于是表荐,悉收其群奴煞之,而立续祖为家。光武拜善为太子舍人,后迁日南九江太守。”[35]可见汉画所刻乃表示李善因其至孝而得成仙,而《真诰》卷十六则保存和阐发了汉代这种孝可成仙的信仰。
汉画中的列女主题亦基于同样的宗教伦理逻辑,即以成仙的至高方式褒崇节义。如《列女传·节义》“京师节女”条:
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报其夫而无道径,闻其妻之仁孝有义,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为中谲。父呼其女告之,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乃且许诺,曰:“旦日,在楼上新沐,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牖待之。”还其家,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楼上,东首开户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而视之,乃其妻之头也。仇人哀痛之,以为有义,遂释不杀其夫。君子谓节女仁孝厚于恩义也。夫重仁义轻死亡,行之高者也。《论语》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此之谓也。[36]
又如1908年出土于山东滕县董家村的“荅子管仲等画像”(天理大学参考馆藏石),有榜题“荅子”、“荅子母”、“荅子妇”等[37]。汉刘向《列女传》卷二《贤明传·陶荅子妻》中载有春秋时陶大夫荅子之妻的故事[38]。荅子妻觉察到丈夫任官只为牟取私利,恐致灭门之灾,劝说无效乃携子离家而去,后果应验。显然,荅子妻能以义易利,同时又能全身复礼,自为汉家所推崇。显然,“荅子管仲等画像”所要强调的主角即“荅子妇”,而贪婪、愚蠢的“荅子”、“荅子母”,既无才又无德,不过是作为“荅子妇”故事画面的表达陪衬元素罢了;武梁祠东壁上“京师(节)女”、“怨家攻者”均出榜题,同样是为了在故事形态中凸显“杀身成仁、义冠天下”的节女的崇高。
换言之,汉画中人物以一组组故事形态出现,目的是为了定位其中的核心人物,让人们从这些最著名最精彩的故事片段画像中,立刻就能看出所要凸显的中心人物,而不是要铺述故事本身。很明显,这些中心人物各因故事片段所表之德而入仙品。
前述沂南汉墓中有苏武与管叔比肩而立的画像,据刘向《新序·节士第七》:“苏武者,故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孝武皇帝时,以武为栘中监使匈奴,是时匈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虽有鈇钺汤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余岁,竟不降下,可谓守节臣矣。……匈奴绐言武死,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义归武,汉尊武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班固认为,苏武是实践儒家“志士仁人”人格理想的典范,慨言:“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汉书·李广苏建传》)汉宣帝时,苏武已成为图画形貌于麒麟阁的11位名臣之一,臻人臣之最。可见苏武的节义获得了汉人何等的尊崇。事实上,他的忠义气节,不仅彰显了汉家臣子之伟岸,更向匈奴蛮夷展示了汉家雄风。毫无疑问,他在汉人心目中,是作为“节臣”之最高标范入列仙品。
根据上述以武梁祠东、中、西壁图像为中心的讨论,以及对汉画超越世俗时空秩序之宗教属性的认识,可以判断,汉画中保存着一套以图像形式出现的“仙谱”;这个仙谱内含的评价标准可以归纳为君明、臣忠、子孝、妇贞、士节,具有“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之功,表现出强烈的“《春秋》决狱”[39]特征。基于此,汉儒刘向撰《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应属实[40],且对应汉画像之内容,皆具一定的“仙传”属性,是时人褒崇忠、孝、节、义者(历史与当朝人物皆在其中)至极致而宗教化的结果。上论《列女传》所见陶荅子妇、京师节女、梁高行等皆以其节义成就完美人格,堪谓“列女”死后成仙之典型,故得图其像而入列仙焉。
事实上,汉武帝时已有画图褒扬贤臣的做法。按《汉书·金日?传》,武帝时“日?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甘泉宫通天台画有天、地、泰一诸鬼神,为通神祭天之处;“汉法,三岁一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太平御览》卷五二七引《汉旧仪》)。可见死后图画于甘泉宫乃愿其升天。又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甘露三年(前51),宣帝感匈奴之宾服,思股肱之美,令图画十一功臣于麒麟阁,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表而扬之。斯乃人臣之最,同具崇高神化意义。故《论衡·须颂篇》云:“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甘泉、麟阁所画,乃汉代价值观之崇高标范;而汉代宗教则承袭、神化汉家标准并从中拣选入列仙谱(如金日?、苏武等)。
三、《真诰》对汉画仙鬼体系的保存与改变
历史上,各种符合汉家道德价值标准的典型人物皆入仙品;武梁祠三面画像所划分的三重仙界,刻画着因生前之德而死后变仙的列仙图谱。汉画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正是汉画人物图像的内在秩序规则,而成之为汉代仙传谱系。可以说,汉画中的历史人物都是生前忠孝节义、死后成仙的典范。同时尤其应注意,汉画对包括众刺客在内的“英雄”人物所持的盛赞态度——甚至夏桀也因勇武而被接受——,强烈地显示出汉人“德”、“力”并重的价值观。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忠、孝、节、义),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长时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的结合,乃是汉代仙谱依以形成的内在思想要素。汉代仙谱以图像的静态表达方式,刻在精心布置的墓内或祠堂,深刻地表达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世界,呈现了他们所信仰的死后人生的可能样态。
对汉画神仙谱系的识读,离不开对汉晋时期仙道文献与思想的理解。实际上,汉画仙谱体系与《真诰》所保存的仙鬼体系,尤其在升仙标准与别秩分类方面有较大的重叠。《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对世人死后成鬼成仙的分类和迁谪标准有如下表述:
夫有上圣之德,既终,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补三官之五帝,或为东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也。
夫有萧邈之才,有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荣贵者,既终,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41]四百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进,以三百年为一阶。[42]
夫有至贞至廉之才者,既终,受书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渐,得进补仙官,以二百八十年为一阶耳。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阳有似也。夫至贞者,纷华不能散其正气,万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务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或易世炼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既终,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馀骨随身而迁也。男留在(引者按:当作“左”),女留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
诸有英雄之才,弥罗四海,诛暴整乱,拓平九州,建号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终,受书于三官四辅,或为五帝之相,或为四明公宾友,以助治百鬼,综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属于三官,永无进仙之冀,坐煞伐积酷害生死多故也。[43]
两相比照,汉画中所见的历史人物大都能够对应纳入《真诰》所划分的几类人群中,表明在升仙标准这一点上,汉画与《真诰》确有较大重合处。基于《真诰》仙鬼分类及武氏祠等比较规整的汉画历史(及传说)人物画面分布形态,部分可识者初步归纳如下(表2):
表2 基于《真诰》仙鬼分类及汉画像历史(及传说)人物分布形态整理的仙谱表
| 标准 | 汉画所见历史(及传说)人物 | |
| 有上圣之德者 | 伏羲(戏)、女娲、祝融(诵)、炎帝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俈)、皋陶、尧、舜、禹、商汤、周文王(伯昌)、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召公、仓颉、容成公、老子、孔子等 | |
| 有萧邈之才、绝众之望者 | 项橐、柳(下)惠、晏子、季札、何馈、颜渊、子贡、伯牙、师旷、伯乐、扁鹊、仓公、赵盾、燕昭王+郭隗+乐毅、孙子(孙武)、范雎(且)、司马相如(长卿)、李少君等 | |
| 有至贞至廉之才者 | 忠臣节士 | 关龙逢、子路、程婴、(公孙)杵臼、伍子胥、苏武、(二桃杀)三士、曹沫(劫齐桓)、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聂政(刺韩王)、荆轲(刺嬴政)、无盐丑女、颜叔子、义浆羊公、魏信陵君+侯嬴、范赎等 |
| 孝子孝女 | 赵苟、丁兰、曾参、申生、闵子骞、老莱子、韩伯榆、邢渠、董永、朱明、李善、卫姬、七女(为父复仇者)、魏汤、原谷、三州孝人、金日?等 | |
| 节妇烈女 | 梁节妇、齐义母、京师节女、梁高行、秋胡妇、鲁义姑、曾母、楚昭贞姜、荅子妻、管仲妻、王陵母等 | |
| 先世有功者 | 晋灵公、管叔等 | |
| 有英雄之才者 | 齐桓公+管仲[44]、鲁庄公、秦始皇、汉高祖+张良、蔺(令)相如、孟贲、乌获、夏桀等 | |
回到本文开头所引沂南北寨汉墓图像,画面下格的“齐侍郎”及“苏武”、“管叔”皆为齐桓公(图像上格所绘)在鬼界的下属,而非生前属官。陶弘景曾提到:“如桀纣王莽董卓等,凶虐过甚,恐不得补职僚也。”[45]管叔为周武王弟(姬鲜),由于反叛而被周公所杀,卒年距东汉晚期的沂南汉画已有一千多年。也就是说,管叔死后在酆宫做鬼官已逾千年,依然只是齐桓公的下级,地位较低,难获升迁。而苏武为西汉忠臣,新死仅二百余年,地位已与管叔比肩。藉此汉画可以看出忠孝之德对于升仙的重要意义。
关于“侍郎”问题,略为解释。按《真诰》卷十二“稽神枢第二”中提到“林屋仙人”王玮玄乃“是楚庄王时侍郎,受术于玉君,右理中监,准职如司马。”[46]对于王玮玄之为楚庄王“侍郎”的这种身份,陶弘景亦曾表示困惑:“若是春秋时楚庄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职。而汉楚王又无庄谥。”[47]事实上陶弘景有所不知,在汉画所表达的汉代信仰世界,所有入列神仙谱系者,必依汉家官僚体系架构,各领其在仙界之职。由此便可理解,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之下何以也有“侍郎”之官。王玮玄为楚庄王侍郎说,至少可以证明《真诰》保存了东汉画像石流行时期某些宗教信仰的模式,汉画与《真诰》间确有图、文互证之缘。
除了依生前贡献的升仙标准,《真诰》还发展出一套严密的仙鬼迁、谪制度。在对不同人等的价值归类升仙方面,大多继承了汉画所见的仙谱价值体系,但亦有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晋人对“诸有英雄之才者”的贬斥。汉画对“英雄”人物,包括众刺客甚至夏桀在内,皆持盛赞态度,故英雄与忠孝节烈在武梁祠同登仙品,而《真诰》则抑黜之,指其“永无进仙之冀,坐煞伐积酷害生死多故也”,与汉人价值观殊甚,是证“汉晋道殊”[48]及终极意义体系变迁之剧。
四、镇星“二十八岁而周天”:仙鬼迁擢标准的古天学依据
上引《真诰》关于死后世界仙鬼迁谪标准中,在年限规定方面,除了300年、400年、1000年之类一般完美大数外,还出现了如下一些看上去令人困惑的年限数字:
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从此渐进,得补仙官,一百四十年,听一试进也。
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
二百八十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渐,得进补仙官,以二百八十年为一阶耳。
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49]
安(案)司命说,启在位二千四百年,得上补九宫。[50]
对于文中所给出的年限标准,《真诰》并未提供任何依据,陶弘景在整理注释之时,亦未给出任何解释。但是,从这组年限标准的数字选择中,还是不难看出一些端倪。除了最后一句提到的2400年以外,其他的三种年数:140、280和1400,它们彼此间是有着倍数的关系,并且它们有如下的一些公约数:1、2、4、5、7、10、14、28、140。从中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组公约数中,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最为有关的一个数字是28,它首先使人想到的就是与古代著名的二十八宿星空划分体制的联系。
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个基础性的星空划分体系。关于它的起源,学界的看法虽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春秋时期以前,甚至周初时期,二十八宿的体制就已经确立[51]。
秦汉时期的传世典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宿各宿名称;呈现二十八宿各宿名称的出土文物时代则更早。20世纪70年代末,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一件大漆箱,箱盖上绘一幅标有二十八宿名称文字围绕北斗的天文图。另一件重要文物是1973年11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证明二十八宿在秦汉时期普遍使用。《五星占》文字计约八千字,分九部分;占文的后三部分记录了从秦始皇六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间共七十年里,岁星、填(同“镇”)星和太白在天空中的位置,并用完整的二十八宿恒星作背景描述了三大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里的动态[52]。这都表明,至迟到秦汉之际,至少对于天文星占家来说,二十八宿的认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道术修炼的周期与天文知识密不可分。太阳的视运动轨迹绕二十八宿运转一周为一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是用完整的二十八宿恒星为背景来记录岁星、填(同“镇”)星和太白在天空中的位置。其中提到岁星(木星)和镇星(土星)的运转周期:木星周期十二年,土星周期二十八年。
在古代关联性思维背景下,土星二十八年的周期,很容易引人将其与二十八宿相联系。《淮南子·天文训》云:“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又《史记·天官书》载,“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岁填一宿”;“(填星)其一名地侯,……二十八岁周天”。而土星每年行一宿,一个完整的周期结束,恰好周行二十八宿一遍,而其行一宿即相当于地上的一年(太阳则恰好行二十八宿一周),这种速度变化上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天上与人间的不同[53]。
取镇星“二十八岁而周天”为基数进行计算,则一周天28年×5=140年,10周天为280年,50周天为1400年。取镇星的5周天、10周天和50周天,意在显示差异。而选10以内的其他数字作倍数相乘,结果都有尾数,形态不够完美神圣。
上文引《真诰》中关于升迁年限的最后一句,“安(案)司命说,启在位二千四百年,得上补九宫。”这里的2400年数值不是28的倍数,与上述计算模式看似不相吻合。但不难发现2400实际上是由1400加1000组合而成,上引《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的迁谪标准第一条就是:“夫有上圣之德,既终,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补三官之五帝,或为东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也。”这样一来,这种计算模式确为两种“仙鬼迁谪标准”计算模式的组合,一种是28为基数的计算模式,另外一种是完美大数的模式。
当然,除此之外,基于某种特别根据——崇高之德,死后亦可超越周天之限而升仙。如《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所述邵(召)公故事:“邵奭为东明公,云行上补九宫右保公。”陶弘景注曰:“前云邵为南明公,今乃是东。若非名号之误,则东南之羌,既寻当迁擢,则必应是启中君脱尔云邵耳,亦可是有甘棠之德[54],故不限其年月耳。”[55]
五、信仰结构变迁与仙鬼谱系存佚
康儒博(Robert F. Campany)提出,古代仙传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特定的知识和文本脉络中产生;这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种种片断文献的任意收装,而是一种“传记再造过程”(higiographic reshaping process),即对现存素材进行有意识的修订、重构和再叙事处理[56]。现在看来,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于两汉时期的仙鬼谱系演变过程之中。
仙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辅教之作;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仙谱、以什么方式对神仙的成仙历程进行叙述,这种造“模”本身不仅表达着一种宗教生存发展和传播的基本策略,更是一个时代的理想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因为这些仙谱,将面对的是可能的信仰人群,如果仙谱和传记中的叙述缺乏与社会现实生活经验的合理接口和某种必要的对峙性(升华)的或批判性的张力,都同样会缺乏共鸣而丧失信众,因为那将缺乏对现实人生的解释力和批判力——两者缺一不可。缺乏解释力意味着令可能的信众找不到与其现实人生的对接点,不能使人生成为修仙的起点——无论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的起点;缺乏批判力则不能为其突破现实人生处境的种种封锁而走向哪怕是彼岸性的自由和终极意义提供依据。
汉墓画像证明,东汉时期的信仰中,忠、孝、勇、信等道德伦理对升仙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到东汉末,道教的倡导者们贬斥死后成仙的旧信仰传统,宣扬不死而仙(生人成仙之道,所谓即身成仙、白日飞升),极力反对杀伐。《太平经》更言:“大恶有四:兵、病、水、火。”这种思想在《想尔注》中亦有多处体现:“兵者非吉器也”;“道故斥库楼、远狼狐、将军骑官房外居,锋星脩柔去极疏。但当信道,去武略耳”;“以兵定事,伤煞不应度,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天子之军称师,兵不合道,所在淳见煞气,不见人民,但见荆棘生”;“为善至诚而已,不得依兵图恶以自疆”;“至诚守善,勿贪兵威,设当时佐帝王图兵,当不得已而有”;“兵者非道所喜”[57]。《太平经》更倡导贪生畏死修道:“天者,大贪寿常生也。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也。”[58]于此便不难理解《真诰》之判: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们因杀伐过重,永留鬼域,而无进仙之冀。陶弘景在《真诰》注释中提到:“文王名昌,《礼》云,年九十七亡。此父子并得称圣德,而不免官鬼,虽为煞戮之过,亦当是不学仙道故也。”[59]承认杀伐之罪会影响死后在阴间的官位,但实际上强调了学道修仙对于一个人死后命运之重要。
神学上的这种转变,涉及成仙的根本性问题。其中,炼丹术本身是一种通过学问的方式,证“仙可学致”,而不再是向鬼神祈求。于是主体的作用上升,得到了更多的肯定。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对待鬼神的态度问题上。秦汉时期,冀仙之士皆得向鬼神祈求,以致大起神祠,众多方士藉之为帝王祈求长生不死。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甚至秦皇汉武也加入方士的队伍,不辞劳苦与危险,东去海上尝试接近神仙世界,梦想从神人求得不死药。这在秦汉历史上形成一种文化逻辑,即人的不死梦想,有待于“外物”之“坚固”来实现;而这个“外物”乃在神人之握。在此逻辑下,即使对于死者,也需要运用方术,与鬼神沟通,甚至用神药在幽冥世界为死者治病、驱除疫鬼,解除灾殃,以图助其早日升仙。在此过程中亦得施用文书,以“三官手书”向主管生死命籍的三官祈求。
这种对待鬼官和神仙的方式正是汉代宗教的主要特征。这种信仰形态,实乃古老的墓葬仪式(如章丘女郎山战国墓乐舞陶俑群所见)同神仙信仰以及最为儒家所倡的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的结合态(如济南无影山西汉墓所见乐舞陶俑群+三官+神吏),它以服务死者、操作死后过程、使死者转变成仙为其核心。这种传统至少要上溯到先秦时期燕齐巫者“羡门”的方仙道,《史记·封禅书》所记方仙道之尸解信仰[60],是其主要形态:“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然而到东汉后期,生人修炼成仙信仰占据上风;加之魏晋玄学冲击、五胡乱华,以及佛教的持续、深入传播,社会价值观念巨变——东晋政权能够接受长期偏安的现实,本身亦表现出与汉家观念的巨大落差。很明显,曾经流行两汉的尸解信仰受到贬斥,《太平经》所崇“贪生”修道不死观念、天师道所代表的生人修仙不死信仰流行,伴随两晋士人新价值观念的发展,许多汉代传统道德标准也被颠覆,曾为汉人推崇的一些古圣贤如今备受士人讥讽(甚至葛洪《抱朴子》亦视比干杀身之忠、尾生为期抱梁而死等为愚蠢之狂举);释天下而求不死,成为新宗教理想。价值观念已然转变,作为昔日价值理想代表的旧仙谱遂不得传;《真诰》所见只是一些隐传下来的线索。因此,虽然《真诰》继承了来自汉代的诸多信仰要素,却难免受到当下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不能完全反映汉代的信仰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价值观、甚至可说是当时社会一般价值观念之极致表达的仙谱,难免发生变异。这应是三代以来英雄圣贤节义之士反而不见于《列仙传》以下各种仙传文献的主要原因。
今传本《列仙传》众仙不见于汉画。此中问题较为复杂,兹略加辨析。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如将元嘉元年(151)所建武梁祠画像之历史人物故事视为当时仙谱文本之固化,则此图像化文本堪为一较古底本以供比较。汉画像石人物不见于今本《列仙传》,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最初《列仙传》或曾有之,但由于仙传文学辅教功能之需,伴随信仰结构变化,难免调整其构成,且后世不止一次的“清整”道教亦难免致文本变化,今人安得睹其旧容?如《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形解销化”句下应劭注引《列仙传》有:“崔文子好学仙于王子乔,(乔)化为白蜺,文子惊,引戈击之,俯而见之,为王子乔之尸也,须臾则为大鸟飞而去。”今本《列仙传》有“崔文子”条但故事已全然不同。又《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应劭注:“《列仙传》陵阳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始出赤黄气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为六气。”亦不见于今本。陈洪认为,汉末“古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应劭的确可以看到并采用某种《仙传》,该《仙传》是东汉末年(约165-204)的产物;而流传到今天的《仙传》,早已不是“古本”的原来面目;在嵇康被杀以前(263),续本《仙传》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了基本定型本[61]。总之汉代以后《列仙传》传本变化甚大,如何才能准确把握汉代《列仙传》的思想形态,为一难题。张美樱提出,“就神仙思想的内容表现上看,《列仙传》的神仙思想较为朴素,在仙道修炼过程上以简单的服食为主,也有仙药的服食,但以遇仙所得的仙药为主,而神仙信仰多与祠庙信仰结合,神仙形象多含有巫者的样貌”[62]。其说或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这已是基于今本的认识。
至于初本《列仙传》之渊源及其文本形态,扑朔迷离,颇已难考。在只言片语之间似乎可看出更早一种名曰《列仙图》的古本。葛洪《神仙传·序》:“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又《抱朴子内篇·论仙》:“至于撰《列仙传》,自删秦大夫阮仓书中出之,或所亲见,然后记之,非妄言也。”唐释法琳《破邪论》引《列仙传》称刘向云:“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创撰《列仙图》,自黄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向检虚实,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矣。”[63]《颜氏家训·书证》指出:“《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64]颜氏所判甚是。至于“创撰”或为“仓撰”之误。今本《列仙传》“玄俗”条下赞称:“余尝得秦大夫阮仓撰《仙图》,自六代迄今,有七百余人。”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校勘本《抱朴子内篇·论仙》提出,“大夫阮仓”四字刻本讹作“太史暨汉”。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即“大夫阮仓”、“太史创”或许是“太史阮仓”的抄误。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杂传”类序:“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阮仓属秦抑或属汉,尚难究竟。但无论如何,若《列仙图》果为秦人或汉人所撰,则汉代当有《列仙》传记行世,则王逸注《楚辞》引古本《列仙传》“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戏沧海之中”之说可与马王堆帛画互证,则可能有刘向据以“检定”而成原本《列仙传》之事,而汉后则历世损益多至难辨,甚疑世本《列仙传》颇有天师道徒之笔矣。
伴随太平道黄巾之乱的失败,以及西部五斗米道张修的类似结局,道门面临严峻挑战,这也是道教内部新思潮即“天师道”崛起的契机。至此,以“新出老君”相标榜的新道派问世,神学的新趋势形成。旧宗教的衰亡和天师道的崛起及其带来的宗教运动,正是仙鬼谱系变化、旧谱系佚失的最重要原因[65]。这同样可以解释,东汉以后西王母及其所代表之仙术地位逐渐下降、老君及其道术地位上升,而且是以老君的自我更新形态“新出老君”来表达。
如此,汉代仙谱的基本结构得由《真诰》存续,吾辈得览其要,幸甚。对比另外两部早期仙谱——《列仙传》与《神仙传》,亦可发现,随着汉晋之际道教的变革,汉画所见神仙标准已发生巨大变化。《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所收《列仙传》记载赤松子、宁封子等自上古至秦汉共七十一位神仙,他们或驭使风雨,或妙手回春,或预知未来,或死而复生,或长寿,或尸解,或服食,或炼丹,或飞升,或变化,或遇仙……,总之皆修仙道,乃有异能之高人。《神仙传》中记载了广成子等八十多位神仙[66]。两相比照,除“容成公”、“赤松子”和“彭祖”与《列仙传》重出外,其他均不相同。葛洪明言非欲否定《列仙传》,只是《列仙传》中所举“盖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及一者也”[67],因其“不可尽载”,故作《神仙传》以为增补。所录仙人多为凡人通过学道而成仙者,以论证神仙可学,不死可得。至于《列仙传》中所举之仙,葛氏“多所遗弃”,不再赘述。
信仰结构的这种变化,导致精神世界的焦点转向自主的神仙修炼模式。这意味着,人——无论死者抑或生者——获得拯救与不朽的方式,超越了对古老的巫师体系的依赖(如解注瓶里的神学),而发展成为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人生追求。至此,道教的神仙信仰终于渗透到了汉人的整个人生过程之中,而不再仅仅是提供给生人的梦想或提供给死者的解脱;进一步说,神仙信仰终于从过去的人生终点,变成了现在的生活方式。于是,整个人生过程就是追求神仙的过程;人生中的一切都成为神仙修炼的可能要素——从山居穴处到冶铸制药、从饮食烹调到人伦道德[68]。《老子想尔注》对旧信仰的批判,也包括对旧的神仙传记的破斥:“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何谓邪文?其五经半入邪,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邪也。”[69]于是汉画造作流行时代的仙谱,伴随汉代宗教体系之变迁而亡佚,吾人只能在出土汉墓资料中去追寻。
道教信仰体系的此种变化在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25)问世的《大道家令戒》中反映尤为明显:
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趣利,强弱忿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者何人?但畏鬼,不信道。故老君授与张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70]
张陵是作为革“言鬼者”之命的代表,作为“人之师”,或者说作为新宗教的化身而出现的。
必须看到,虽然旧的宗教体系受到“新出老君”信仰者的斥责,而事实上作为一种长期被接受的宗教传统,其变革并不意味着此后旧宗教传统的彻底消失,而是汇入后世道教之中,成为其神学的一部分,只是地位发生了由主到辅的转变。譬如《神仙传》对诸多“托形仙去”的旧宗教传统,仍多收录,尽管是以变相(赘之以修道炼丹或得丹)的叙述,此乃过渡期道教所无法避免。
综上,汉墓图像多见的不同时空之历史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的空间乃具有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性特征。以秩序严整的武氏祠东、西、后壁图像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资料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汉代“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因此,汉画中内在有序的历史人物图像,当更合理地作为汉代仙传谱系予以对待。进一步说,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以及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的深度融合,乃汉代“仙谱”所依以形成的关键思想要素。同时,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作为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之际的价值观念遽变发生转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以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无疑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本文第一、二节的基本稿刊于日本东方学会《东方学》第129辑(2015年1月)。作者谨向提出宝贵意见的日本东方学会匿名查读专家致以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武田时昌先生、三浦国雄先生、Norman H. Rothschild博士、小幡满博士、许洁博士、朱磊博士、冯渝杰博士及博士生向群的帮助。
注释:
[1]关于《列仙传》与《神仙传》的研究,参见Robert Ford Campany,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Max Kaltenmark,tr.Le Lie-sien tchouan:Biographies legendaires des immortels taoistes de l’antiquite(Beijing:Universite de Paris,Publications du 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Pekin,1953;1987 reprint Paris:College de France).Robert Ford Campany,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Benjamin Penny,“The Text and Authorship of Shenxian Zhuan,”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4,2(1996):165-209.宫泽正顺:《『列仙传』と『神仙传』について》,《儒道佛三教思想论考:牧尾良海博士喜寿记念》,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91年,第213-242页。蒲慕州:《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汉学研究》第8卷第2期,1990年。福井康顺:《神仙传考》,《东方宗教》1951年创刊号;《神仙传续考》,《宗教研究》1954年第137号;《列仙伝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57年第3号。小南一郎:《〈神仙传〉の复元》,收入《中国文学语学论集——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向群:《〈神仙传〉版本考》,《文史》2014年第4辑。
[2]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6页。
[3]曾布川宽先生广泛讨论了两汉时期不同区域的升仙图,但认为武梁祠画像中的“历史故事”(孝子、列女、刺客等)“有可变的要素”,所以采取了“暂且留下不论”的态度。见曾布川宽:《汉代画像石における升仙图の系谱》,《东方学报》第65册,1993年,第132页。土居淑子专题讨论了中国古代的仙界图像,见土居淑子:《古代中国における仙界图像》,《美术史研究》第8册,1971年,第17-39页。信立祥指出:“汉代祠堂里所有的历史故事画像并不是雕造者或祠堂所有者自由选择和创造出来的,而是严格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选择和配置在祠堂里。”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4]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23页。该书第40页又说“管叔”、“苏武”等“是乱刻的”。该报告认为该墓造于东汉晚年、公元193年以前,见该书第67页。
[5]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下),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01页。
[6]汉墓中多见如是文字:“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泰山。”“生属长安,死属太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相关讨论参见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
[7]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东壁朱书“诸欲观者皆当解履乃入观此”,西壁朱书“诸观者皆解履乃得入”。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古来墓葬多忌讳;“解履乃入观”之所指,应非一般性质的观看,而是墓葬封闭使用前一些人短暂的观摩或祈拜性质的进入。
[8]费振刚等校点:《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8-529页。
[9]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74页。
[10]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页。
[11]除了图像资料,汉代史籍文献对于上古圣人的怪诞身形亦有明确载述。如《白虎通义·圣人篇》云:“圣人皆有表异。《传》曰:‘伏羲禄、衡连珠、唯大目、鼻龙伏,作《易》八卦以应枢。黄帝颜,得天匡阳,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颛顼戴午,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摇。帝喾骈齿,上法月参,康度成纪,取理阴阳。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舜重瞳子,是谓玄景,上应摄提,以像三光。’《礼》曰:‘禹耳三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决河疏江。皋陶马喙,是谓至诚,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纬书《尚书帝命验》云:“禹身长九尺有余,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曰:“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分见班固纂辑,陈立疏证,吴则虞注解:《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7-339页;[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吕宗力、栾保群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9页;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12]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13]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65页。
[14]蒋英炬:《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49(西壁)、图50(东壁)、图51(后壁)。
[15]有关武氏祠图像内容的整理,可参阅长广敏雄编:《汉代画像の研究》第二部“武梁石室画像の图像学的解说”,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5年,第61-95页;黑田彰:《武氏祠画象石の基础的研究(三)》,《京都语文》第16号《中世特集》,佛教大学国语国文学会,2009年11月,第64-176页;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265-330页。据之可整理列表(见表1)。
[16]洪适《隶释》卷十六“武梁祠画像”条载:“所画者古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各以小字识其旁,有为之赞文者。”见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8页。
[17]与多数学者所持的“政治教科书”说不同,巫鸿认为,帝王图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传统上被称作‘三皇’的伏羲(和他的配偶女娲)、祝融和神农。第二组中的帝王与《史记》记载的五帝相同……最后两位——禹和桀组成第三组,二者分别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的创立者和末代君主”。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174、181页。巫鸿的说法亦未解决问题。
[18]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6页。
[19]《汉书》卷九《元帝纪》记汉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20]武利华主编:《徐州汉画像石》,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图124。该画像石系铜山县洪楼东汉祠堂三角隔梁。
[21]参阅增渊龙夫:《汉代における民间秩序の构造と任侠的习俗》,《一桥论丛》26-5,1951年,收入新版《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77-118页;东晋次:《汉代任侠论ノート》(之一、之二、之三),《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第51、52、53卷,2000、2001、2002年。
[22]这里需注意,董仲舒“《春秋》以为戒”的说法出现于西汉时期,到东汉宗教化以后作为鬼神世界的夏桀,已与董仲舒所表达的世俗“教材”属性产生较大差异。
[23]蒋英炬、高文:《中国美术全集18·绘画编·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258。另,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参考馆藏有一方汉代空心砖,上刻三人共坐,从其人物形态及组合模式分析,内容应与此砖同。该砖图像见《天理大学附属参考馆藏品》第1期第3卷《画像砖》,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6年,图版31。
[24]燕昭王、乐毅、郭隗的相关事迹,参见《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卷八十《乐毅列传》。
[25][26][35][45][46][47][55][59]《道藏》第2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3、587、586、587、562、562、585、580页。
[27]这与郑州出土汉画像砖上,郭隗居中、乐毅和燕昭王在其左右的情况,并不矛盾。不难理解,作为当时社会信仰主导的汉儒梦想担当良辅之任,以成就明主和英雄;这应是郭隗——犹如管仲在齐国——居中的原因。至于汉画所载,同东晋许翙抄写《剑经》所论尸解成仙人物(注意《剑经》应不止于论剑,而是更多地论及剑解),恐怕已有不同。大概《剑经》作为文本所记多系最为著名人物,《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记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求仙事,史上著名,亦为仙家所崇,故可理解《剑经》提及燕昭王成仙事。或者许翙只是依其兴趣选择性地抄入《剑经》序中,而其他成仙人物则被略过,遂不显于后世文献。
[28]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2页。
[29]《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道藏》第20册,第587页。
[30]刘云涛:《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文物》2005年第3期。
[31]《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2页“老子、孙武画像”。
[32]《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第106页,图112。
[33]见徐文彬等:《四川汉代石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80、81。
[34]有关事迹见《东观汉记》卷十八传十三、《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李善》。
[36]刘向:《古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2页。
[37]亦可参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年,图54。
[38]刘向:《古列女传》,第47-48页。
[39]《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精华》:“《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40]关于刘向作《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三传及其辑佚整理,参见熊明《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及《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文献》2003年第2期),饶道庆《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增补》(《文献》2007年第1期)等。刘向《新序》亦以不小篇幅专述“节士”。
[41]《道要灵祇神鬼品经·善爽鬼品》引《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云:“夫有萧邈之才,有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荣贵者,既终,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道藏》第28册,第391页)此经或即陶弘景注《真诰》时多次提到的《剑经》。
[42]陶弘景注:“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从主者以去,是入仙阶,不复为鬼官耳。”《道藏》第20册,第587页。
[43]《道藏》第20册,第586-587页。
[44]齐桓公与管仲在汉画中有相当高的地位,而文献所见当时人们对桓公与管仲亦有极高评价。如司马迁引刘安《离骚传》评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衡·书虚篇》赞曰:“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宁戚于车下,责苞茅不贡,运兵攻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论语·宪问》记录孔子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48]开元年间唐玄宗语,见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五《礼仪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3页。
[49]《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道藏》第20册,第586-587页。
[50]《真诰》卷十五《阐幽微第一》,《道藏》第20册,第580页。
[51]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52]关于《五星占》更为详细的内容,可参见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6-58页。
[53]内在地模拟周天过程,成为后世道教之乘斗、“历度天关”存思修炼模式。如早期上清派重要经典《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变经》(约出东晋)之《运度天关披神洞观秘文》说:“帝君曰:子欲飞腾上造金阙,当修洞观,运度天关,……每以夜半,露出中庭,仰存北斗七星朗然,思见我身在斗中央,随斗运转,历度天关。”《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变经》,《道藏》第33册,第564页。
[54]所谓“甘棠”的典故,指周朝召公之德。按召公奭系周宣王时名相,曾出巡南国,惧扰民生而舍于甘棠树下。既去,民思其德政而无所遗加,遂爱其树,诗以咏之,见诸《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发。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56]Robert Ford Company,Making Transcendents: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11,217.
[57]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39页。
[58]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3页。
[60]关于战国及汉初的“道者”及其尸解信仰,参见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61]陈洪:《〈列仙传〉成书时代考》,《文献》2007年第1期。
[62]张美樱:《列仙、神仙、洞仙三仙传的叙述形式与主题》,《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6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66页。
[6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84页。
[65]以此为观念基础形成历代官方认定的道教起源叙事模式,长期构成对作为道教前身的旧宗教历史和相关文献及信息的排斥态度,不仅造成历史信息的混乱,而且似曾导致其后官方史家的排斥性修订。
[66]今见百卷《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神仙传》各收录神仙传记84篇,明代辑本《汉魏丛书》本收录92篇。各版本性质及条目研究可参见上文注引相关文章。
[67]葛洪:《神仙传序》,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
[68]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卡西尔说:“一切较成熟的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之一,就是要从最原始的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之粗糙素材中提取它们的新品质,提取出它们对生活的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69]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22页。
[70]《道藏》第18册,第236页。注意此处“道伤”不宜与后面文字断开理解。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教授)
(来源:《文史哲》2015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